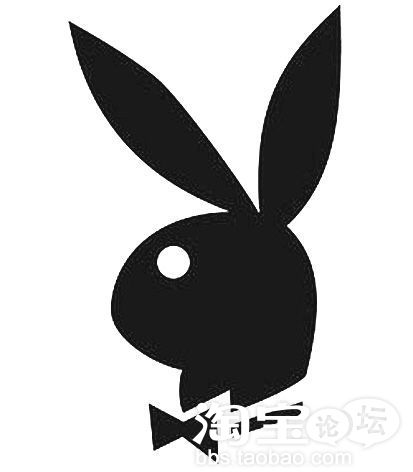
很不幸,《花花公子》在中国只是个传说,由于传说而变成妖魔、变成洪水猛兽。
《花花公子》被拒于国门之外,因为它是一本****。然而“成人”一词,在中国的含义从来没被明确界定过。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,“成人”经常作为一个限定性名词,和“用品”联系起来,以区别于婴幼用品、妇女用品等等。“成人用品”的概念,可以从城市的成人用品店里获得明确的感官印象——昏暗的小巷,逼仄的小黑屋,闪烁的霓虹灯,鬼鬼祟祟的顾客,暴露的图片以及各种超越常规的性用品。这里的“成人用品”一词,完全可以用“性用品”来代替,“成人”和“性”画上了等号。《花花公子》既然被命名为****,理所当然,就被划入“扫黄打非”的领域,包含着*秽的汁液,不仅有碍观瞻,而且有毒于社会。
在理想的设计中,中国社会是一个纯洁的社会,儿童需要保护,成人也需要保护。
中国成人的“被保护”,最明显地体现在性方面。最近总有大学生向有关部门写信,声称受到网络色情的毒害,要求限制网络的开放,加大对大学生的保护力度。这是一个莫大的讽刺,“成人”的概念,一方面在中国被曲解为“性”,另一方面,又表现为像婴儿一样的纯洁。作为****的《花花公子》,被“中国式成人”拒之门外,在这里就获得了充分的根据。 撕掉裸女,它是一本文学杂志 《花花公子》的确有性,主要体现为中页的裸女图片和“当月玩伴”栏目。这也是《花花公子》最大的卖点之一。但如果认为《花花公子》只有“性”,类似于街角的成人用品店,就是误读了,一叶障目,不见森林。
《花花公子》是一本****,明确点儿说,是一本办给成年男性看的杂志。在办刊宗旨上,《花花公子》可谓和《纽约客》平分成人读者市场。《纽约客》最初定位的目标读者群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妇女,《花花公子》的目标读者群则是中产阶级职业男性。《花花公子》的创办人赫夫纳在创刊号上如此描述:“我们应该享受这样的生活:在自家公寓中,调上一杯鸡尾酒,准备两份开胃小吃,唱机里放上一段音乐,邀请一位红粉佳人,静静地谈论毕加索、尼采、爵士乐,还有性。”毕加索、尼采、爵士乐和性——艺术、哲学、音乐和性,这就是《花花公子》的全部内容,也是赫夫纳所认为的中产阶级职业男性,一个男性成人,所应该关注的话题。遗憾的是,《花花公子》和《纽约客》在中国的命运截然不同,成人男性阅读的前者变成了色情杂志的同义词,成人女性阅读的后者却变成文化品位的象征。
除了裸女图片(拍摄这些裸女的摄影师,相当一部分是当代摄影史上的领军人物,比如赫伯特·牛顿),《花花公子》的特色还表现在它的小说和名人访谈上面。它的作者群,实际上就是一支近50年来美国乃至世界文学的“梦之队”。
据说,中国小说家王朔遭到过《花花公子》的退稿,因为写得“太黄”。可见,《花花公子》不刊登《肉蒲团》《金瓶梅》。《花花公子》的作者群,有很多是已经进入文学大师殿堂的文学家:博尔赫斯、纳博科夫、加西亚·马尔克斯、厄普代克、索尔·贝娄、菲利普·罗斯、诺曼·梅勒、冯尼古特、凯鲁亚克、詹姆斯·鲍德温……如果把那些裸女图片撕掉,《花花公子》将是世界上最豪华、最有品位的文学杂志之一。固然,性是成年男性的必需品,高品位的文学,却是有品位男性的必需品。品位不仅表现于豪车红酒,也表现于文学、音乐和哲学。这是《花花公子》的“四杆大旗”。 大人物曾经登场 品位还表现在对社会的关注,这可以从《花花公子》的访谈栏目中看出。《花花公子》的采访对象,都是大人物,很多是政治人物或有争议的人物。它不仅采访了美国总统卡特,也采访过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古巴的卡斯特罗,既采访过已经成为“圣人”的民权领袖马丁·路德·金,也采访过充满争议的马克西姆·X、萨特和约翰·列侬。作为从来没有目睹过《花花公子》真面目的中国读者,很难想象这些人物会出现在一本“成人刊物”上面,毕竟,在中国的语境里,“成人”等同于*秽、色情。
美国是一个多元文化杂糅的国度,最初,清教徒因为遭受到思想迫害而从欧洲大批移居美洲新大陆,对“思想自由”的保护便成为美国的建国理念之一,这表现在美国宪法中的“言论自由”。另一方面,清教徒又有着明确而清晰的道德观,这体现在成人对自我行为的约束上面。“肉体须谨慎,思想须放荡”,这几乎便是《花花公子》得以生存并在美国发扬光大的环境。
评论内容:发表评论不能请不要超过250字;发表评论请自觉遵守互联网相关政策法规。